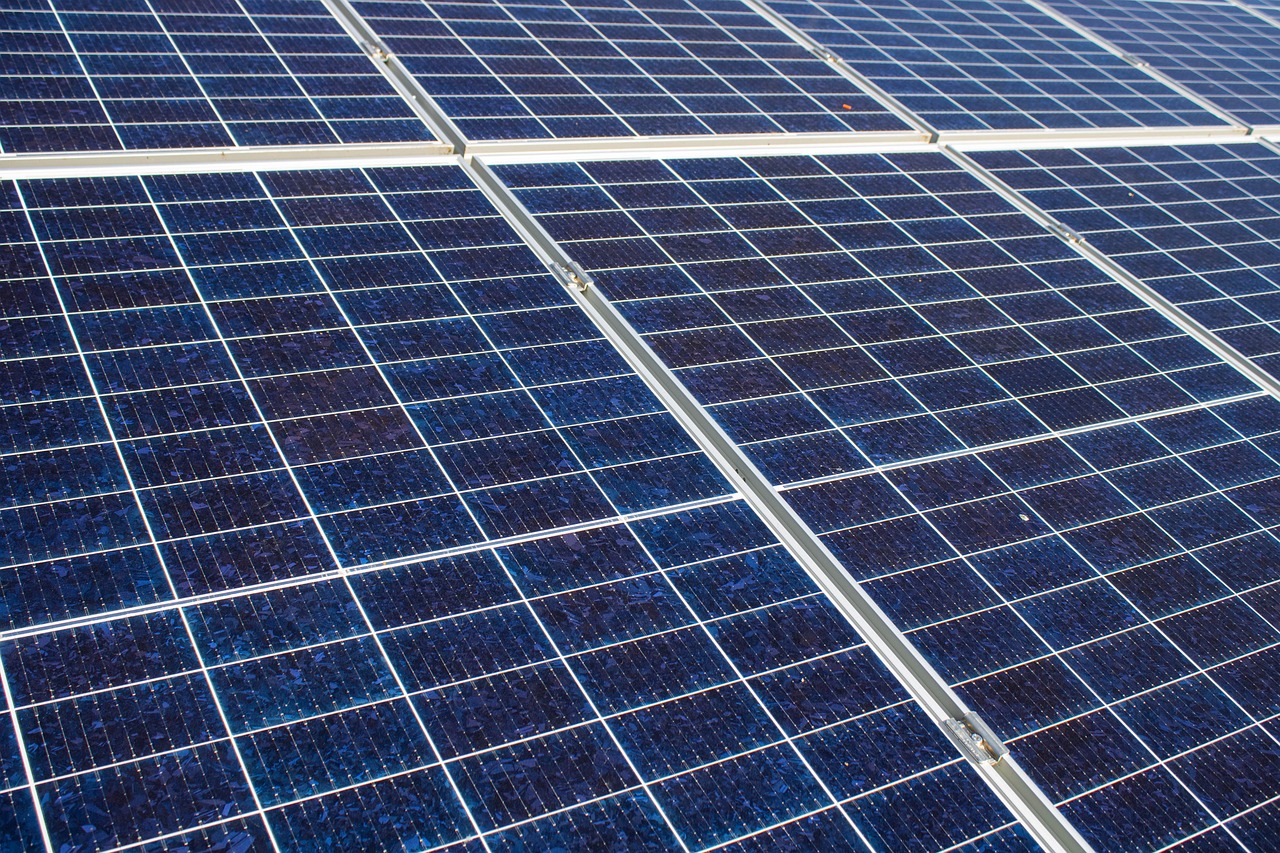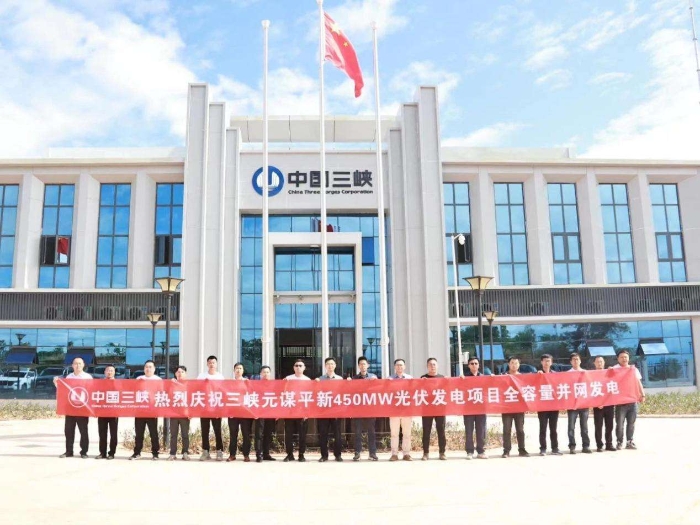“‘華龍一號’的批量化建設已經在進行。”兩會之際,全國人大代表、中核集團戰略與管理咨詢委員會委員劉巍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福建的福清、漳州,兩廣的防城港、太平嶺,浙江三澳,海南昌江,“華龍一號”隨我國核工業“春天”的到來而多點開花。走出國門的巴基斯坦卡拉奇兩臺“華龍一號”機組也進展順利。

“華龍一號”全球首堆福清核電5號機組在今年年初投入商運,打破了三代核電首堆必拖期的“魔咒”,向世界彰顯了中國自主核電技術的優勢。作為工程總承包方中國核電工程有限公司原總經理,劉巍親歷華龍首堆的建設。在他看來,“華龍一號”的成功并不只是核行業的驕傲,而是國家整體工業水平的反映。
“核電是一個系統工程,‘華龍一號”的供貨單位有5300多家,所以核行業的發展能夠帶動促進其他行業發展。”劉巍說,“例如核級電纜就可以促進材料工藝的創新發展,機械設備方面也是一樣。”“華龍一號”的設備國產化率達到了88%,“這一比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沒有國產化的設備只是沒必要自己生產,不構成制約性的問題。”
與此同時,劉巍也清醒地意識到,“雖然我國核電整體上進入了第一方陣,但并不意味著所有技術都在第一方陣。”
— “領跑”,要把標準掌握在自己手里 —
回顧從業的數十年,劉巍從進入二機部二院開始,經歷了核工業發展的一段停滯期。“那時做垃圾焚燒項目,設計大學、醫院等,在啤酒廠的工程設計上二院一度占據了全國2/3的市場份額。”后來去到大亞灣終于接觸到核電站,但“所有的設備都是人家的,甚至對收縮率有要求的水泥都是從法國運過來的。”
“30多年間從第一個核電站起步,到今天能夠建設自主的三代核電,與核電先進國家實現‘并跑’,我國核電的發展速度非常快。”憶往昔崢嶸歲月稠,劉巍的話里流露作為核工業奮斗者的由衷自豪,不過他緊接著說道,“但是現在主流的核電技術標準還不是我們制定的,我們離國際一流還有一定差距。”
從“并跑”向“領跑”發展,會發現“很多現有標準對我們是不適用的”。“比如現在我們研發的成果還要到英國去認證,因為英國是老牌的核電國家。雖然中國連續不斷地建設了幾十年核電站,英國很久沒建,但它可以說你的東西不符合我的標準。”
劉巍舉了核電廠外圍5公里的規劃限制區為例,“這不是中國人提出來的,國際上也不是今天提出的,而是幾十年前就提出來的。”國外近些年來核電發展相對緩慢,“因為沒怎么發展,所以它不著急修改標準。而中國現在發展得快,沿用過去的標準受到的影響就大。”
“我國核電發展至今,到了需要建立標準的時候,也具備建立標準的基礎,應該對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劉巍表示,“到未來實現‘領跑’時,中國的標準就是最好的標準,國外技術和設備進來的話需要通過我們的標準!”
他說,目前“我們還不敢隨便改標準”,并不是缺乏能力,但更改設計標準需要進行大量實驗,“標準的背后是大量的技術積累作為支撐,從材料、制造、設計到軟件分析等方方面面都需要大量的投入”。首先需要全國同行達成共識,“把握我們處于第一方陣的定位,并以此來思考每件事情,抓緊推進相關工作,在重點領域進行突破”。
“十三五”期間,中核集團已組織建成“華龍一號”型號標準體系,一項國際標準提案在國際電工委通過審查并正式立項。“十四五”期間將推廣華龍型號標準在國內外核電項目的應用,繼續推進國際標準的立項和編制;同時將立足主要產業、技術優勢和發展需求,從核電站的總體設計、無線通信、智能控制等高新技術領域組織開展國際標準梳理、申報及相關國際交流,研究并制定具有行業引領性的核電、核化工、核燃料等領域標準體系建設。
“我們絕不妄自菲薄,但我國核工業離世界一流還有一段路要走。”從掌握和發展核心技術的角度,劉巍進一步詮釋了“華龍一號”批量化建設的意義,“正因為還有差距,我們更應該發展我們自主的東西。”
— 兌現減排承諾的主力軍 —
除了帶動國家工業科技水平的整體提升,核電本身是作為一種重要的清潔能源服務社會的。
全球面臨氣候變化的共同挑戰,習近平主席向國際社會承諾的“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對我國加快構建清潔低碳能源系統提出了革命性要求。“核電是未來新增非化石能源中最具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兌現減排承諾、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戰略部署的必然選擇。”劉巍表示。
低碳是核電作為能源的突出優勢。核能是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最小的發電技術之一。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的評估報告中指出,在考慮鈾礦采冶及核電站退役治理后,核能依然是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最小的發電技術之一。國際能源署(IEA)的研究表明,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核電幫助降低了二氧化碳的長期排放增加速度,尤其是在發達國家。
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1~12月全國累計發電量為74170.40億千瓦時,運行核電機組累計發電量為3662.43億千瓦時,占全國累計發電量的4.94%。與燃煤發電相比,核能發電相當于減少燃燒標準煤10474.19萬噸,減少排放二氧化碳27442.38萬噸,減少排放二氧化硫89.03萬噸,減少排放氮氧化物77.51萬噸。
穩定是核電另一個毋庸置疑的優勢。有一種觀點認為,儲能技術的突破將改變風電和光電無法穩定供應的弱點,從而影響核電的競爭力。對此,劉巍認為:一是大規模儲能仍然存在穩定性問題;二是風電和光電本身的制約因素也不只是穩定性,還有占用大量土地資源等環境因素;三是儲能技術的發展對于核電并不一定是壞事,“一旦儲能做好了,核電站也許就不用建在人口密集區了,相應標準就可以降下來,安全成本也就大大下降。”他強調,“技術都在發展,分析問題時不要光盯著別人的技術發展,忽略了我們自己的發展。”
其實對于核電和其他清潔能源,劉巍認為并不是互斥關系,能源多樣性才有利于保障能源安全。“每種能源從來源到最終發揮作用,整個鏈條上受到各種客觀因素的制約。這些制約因素對于不同能源來說是不一樣的。所以不能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邊,否則一個因素變化后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
與多元化、平衡的理想能源結構相比,現實情況則是我國核電占比偏低,“上個世紀末至本世紀初這段時間,全球來看核電發電量占比在10%左右。我認為對我國而言10%到15%的比例是比較合適的,但目前不到5%。作為一種基荷電源,核能應該發揮更好的作用。”
“建議政府部門研究制定《中國核電發展戰略》,強化核電發展頂層設計,統領我國核電發展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規劃,批量化建設自主三代核電機組,助力我國履行‘碳達峰’‘碳中和’國際承諾。”劉巍表示。
— 反對者、懷疑者、受益者 —
盡管核電具有安全、經濟、高效、低碳的優勢,但“鄰避效應”等涉及公眾溝通的問題仍然制約其發展。
被問及一些發達國家“棄核”的決策時,劉巍認為,歐洲一些國家從工業革命到現在,走向以第三產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對能源的需求相對偏低。但即便如此,由于核能不可替代的優勢,“棄核”的計劃往往還是被一推再推。所以那些國家提出“棄核”口號“更多是政治因素在里邊”,“選擇一個公眾最不了解的東西來反對,最容易讓大家接受并獲得政治支持,上臺后因為經濟發展問題又陷入矛盾。就像德國號稱堅決不建核電站,結果用的是法國的核電。”
“對于這種現象,我們應該好好研究他們提出‘棄核’以后,今后的路怎么走。從目前來看,歐洲‘棄核’的結果并不理想。”劉巍說,“如果他們‘棄核’以后走得好,我們也可以走。雖然從事這個行業,但我們是站在國家利益的立場去做判斷。”
對于后處理這一關系到核電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劉巍顯示出篤定和信心:“我們的后處理方式和核電先進國家沒太大區別。伴隨整個工業水平的不斷提升,等到我國核電站迎來退役時,我們的后處理技術將會比他們更加先進。”支撐其信心的,是我國核行業一直沒有停止過后處理研究,“在后處理方面,原來的需求還有限,但也一直在發展中。所以我國后處理能力是有的,體系也是完善的。只是有待通過一些大的項目來體現出這個能力,因為還沒到時候。”按照商運年份和設計壽命來推算,我國核電機組還要數十年才會迎來退役高峰。
談到消除社會公眾對核的疑慮,劉巍坦言沒有什么特別有效的辦法,“事物的理解需要一個過程,一再強調核電的安全性也沒有用,對方可以說還有事故的可能性,為什么要到我這里發展,會影響我這邊開發房地產的。”
雖然實際情況是,發展核電對地方而言,除了發電外還能促進經濟發展。“眼見為實,建完核電站以后當地人就明白了。秦山核電附近的海鹽人沒有覺得核電站不好。深圳這么發達的都市,離核電站大約50公里,他們也沒有生活在恐懼之中。再如國外塞納河邊的核電站,離巴黎市區只有幾十公里,當地人也不擔心。”
“已經建核電站的地方都是核電的受益者,而從來沒有核電站恐懼癥。”劉巍總結道。
2030年碳達峰,意味著GDP增長不再依賴碳排放增加,能源需求必須依靠非化石能源來滿足。劉巍說,“目標分解的壓力之下,各個省市其實都在考慮能源結構的調整問題。地方政府可能會優先考慮風、光和其他可再生能源,不會把核電作為那么靠前的選項。所以核電行業要謀求發展,當下首先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過去三十余年我國核電從無到有,到自主建設大型商用核電站,再到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的自主化,取得如此成就,劉巍認為一方面是依靠大量科技工作人員的艱苦奮斗,“小到每一個核級的螺絲釘,都需要標準、實驗、質保體系等,需要大量辛勤的勞動、細致的工作”;另一方面,“核電發展每一步的重大決策,都依賴決策者的眼光、勇氣和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