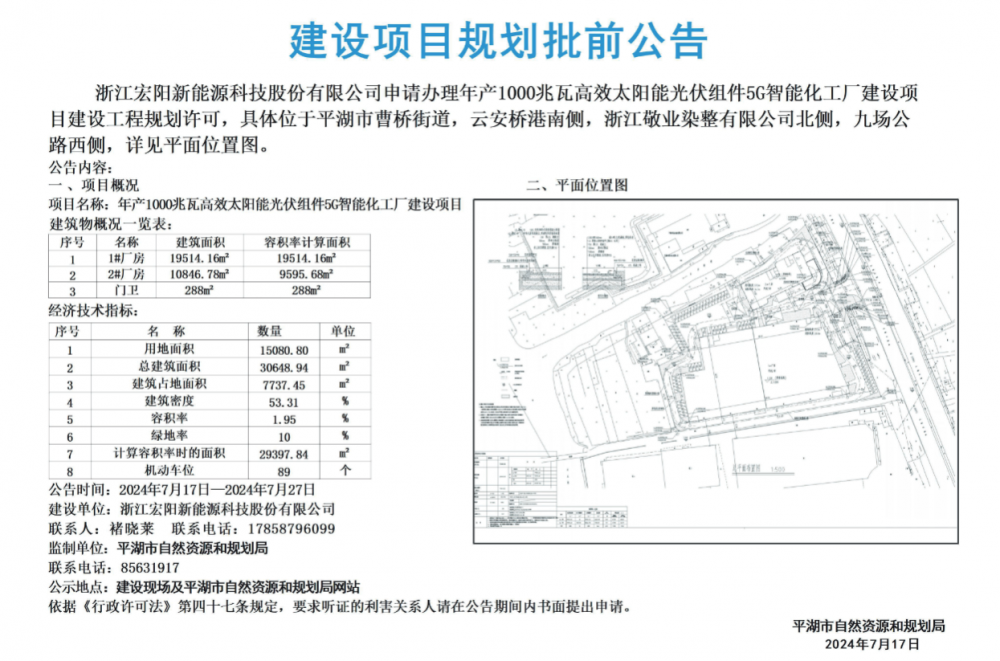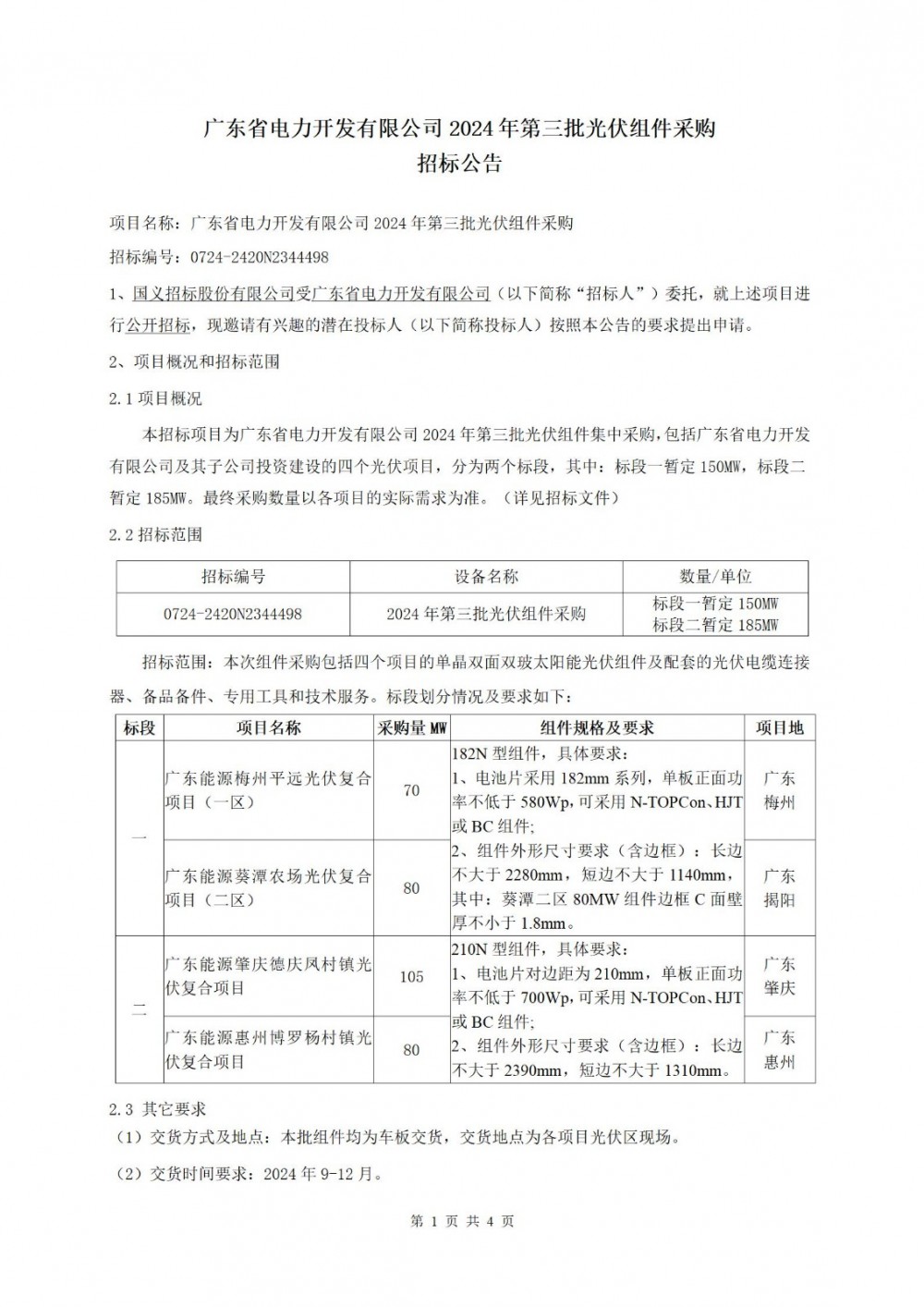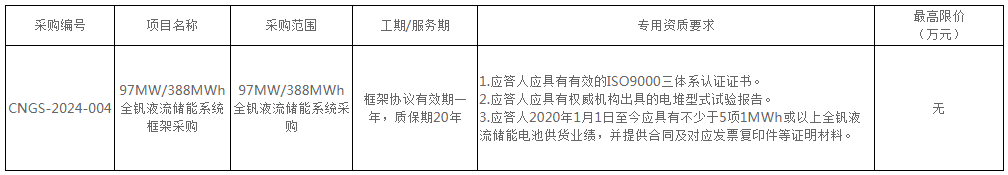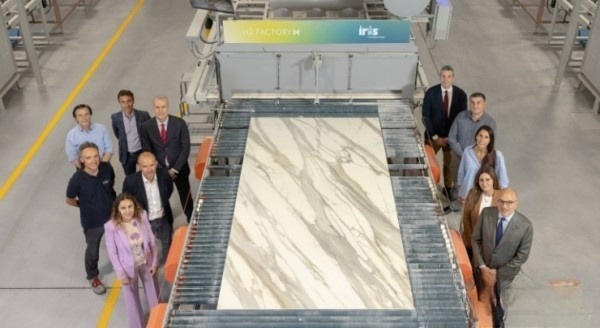煤電供給側改革近年取得了顯著成效,仍有必要繼續實施,優化存量煤電,主動減少無效供給。
隨著“2030年碳排放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的提出,以及“十四五”能源規劃出臺在即,煤電再次置身能源轉型的“風口浪尖”。
由于資源稟賦以及煤炭的物質特性,煤炭生產、加工、利用等環節產生的碳排放是我國碳排放的主要構成部分,尤其煤電占據了排放“大頭”。
“十四五”及更遠的未來,煤電將達到什么規模、扮演什么角色、選擇什么技術路線……對于這些疑問,答案已漸清晰。
煤電碳減排壓力巨大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實現碳中和的時間減半,難度加倍,任務艱巨。”全球能源互聯網發展合作組織經濟技術研究院院長周原冰近日公開表示。
據國網能源研究院能源規劃所主任工程師張富強介紹,我國未來可能將承受更多來自碳減排的國際壓力。“在電力領域,多個歐洲國家已實現零煤電或提出明確的煤電退出計劃。”
“對應碳中和目標,意味著單位供電碳排放必須從600克/千瓦時下降到100克/千瓦時,甚至50克/千瓦時。”周原冰直言,要實現2030年碳排放達峰、2060年碳中和目標,我國煤電裝機必須在“十四五”達峰,并在2030年后快速下降。
作為目前乃至中長期我國電力供應的主力,煤電的生產方式決定了其必然會產生大量二氧化碳,而碳捕獲、利用與封存(CCUS)被視為解決這一短板亟待突破的技術。“華潤電力海豐公司建設了年產2萬噸的碳捕集項目,為氨法、膜法兩種技術路線搭建了實驗平臺,希望能夠尋找到更加經濟的材料、技術路線,以期降低碳捕集成本。”華潤電力海豐公司辦公室副主任王曉東介紹。
不過,CCUS技術目前尚未展現出足夠的商業化可行性。“根據目前情況測算,煤電應用CCUS將使能耗增加24%到40%,投資增加20%到30%,效率損失8%到15%,綜合發電成本增加70%以上。”周原冰指出,CCUS在實現碳移除、碳中和中不可或缺,但在煤電領域難有大規模應用可能。“即便沒有CCUS,煤電未來的競爭力都將大大減弱,其難以承受CCUS帶來的成本大幅增加。”
裝機規模標出 “限高”
據統計, 截至2019年底,我國煤電裝機達到10.4億千瓦,2019年煤電發電量4.6萬億千瓦時,在各自總量中分別占比52.0%、62.3%,較“十二五”末下降7個百分點和5個百分點。
占比雖在下降,但煤電規模仍保持在較高水平。而在電煤價格持續高位運行、煤電利用小時數大幅下降、降電價政策持續推進等因素疊加之下,煤電經營形勢不甚樂觀。根據業內專家提供的數據,2018年,全國15個省區的煤電整體虧損,五大發電煤電虧損面超過50%;2019年五大發電集團公司整體經營形勢有所好轉,但除國家能源集團、華電之外,其他三家集團的煤電業務虧損高達100多億元。
無論是已趨過剩的供需形勢、艱難的經營環境還是來自碳減排目標的約束,均為未來5至10年甚至更長時間內煤電的裝機規模標出了“限高”。針對不同情景,專家分別提出了11億千瓦—13億千瓦的煤電裝機峰值預測。
“煤電供給側改革近年取得了顯著成效,仍有必要繼續實施,優化存量煤電,主動減少無效供給。”華電集團副總法律顧問陳宗法指出,煤電產能過剩仍是發電行業的“風險源”,煤電要實現脫困、轉型,增量要嚴格控制,存量要先完成淘汰關停與重組整合,再分類實施升級改造。“從企業的角度,希望國家能建立起幫助煤電退出、促進能源清潔轉型的公平長效機制。”
煤電“十四五”定位需謹慎
盡管業內專家對煤電規模峰值的預測仍有較大差異,但均對“十四五”期間挖掘存量煤電潛在價值的重要性表示認同。
張富強指出,“少新建,多延壽”是發揮存量煤電作用的重要途徑。“按30年設計壽命計算,2020-2030年將有1.4億千瓦煤電機組退役,2030-2050年則高達9億千瓦。從國際經驗和我國早期投產煤電機組來看,煤電機組服役40-50年是可以實現的安全運行壽命。”
對此,華北電力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袁家海表示認同。他認為,不能單純以現有技術、資源為框架來思考2030年、2040年煤電的功能和作用。“例如,當交通領域電氣化水平大比例提升后,電動汽車本身將成為重要的電力系統靈活性資源,而非只能靠煤電來提供靈活性。”
此外,陳宗法強調,“十四五”規劃制定時應該防止出現“兩個傾向”。“一個是為了實現2060遠景目標,幾乎全部只發展新能源;另一個是把‘十三五’末安排的煤電進度照單全收,不加以限制。兩者都不可取。”
“如果看不清近期路線,就該多看看遠處的目標。”針對業界對煤電未來發展道路的爭議,周原冰認為,能源電力企業應該把握住能源轉型的大趨勢,未雨綢繆,加快運營模式和經營管理的創新,在新的市場環境中找準定位。
華北電力大學近日發布深度報告《新冠疫情后的中國電力戰略路徑抉擇:煤電還是電力新基建》。報告用規劃模型模擬了“十四五”時期電力行業的三條發展路徑:電力傳統基建規劃情景、電力新基建規劃情景、和電力氣候規劃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