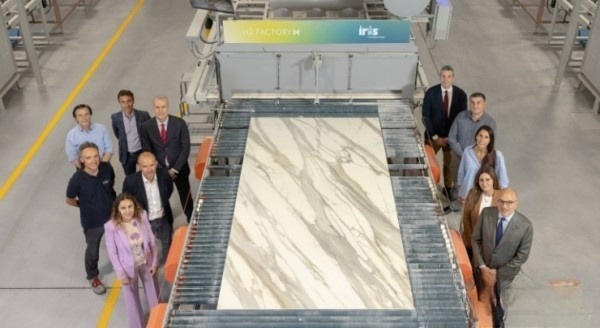俄烏沖突升級后,沙特、阿聯酋等海灣阿拉伯國家成為美國、俄羅斯同時試圖拉攏的重要對象。美英等國一直催著這些中東產油國增產,以壓低油價,這樣做的目的無疑是對制裁中的俄羅斯釜底抽薪。但沙特等國的應對并不十分積極,有限增產并沒有拉低國際油價。在俄羅斯外長5月先后訪問阿曼、巴林、沙特阿拉伯等海灣產油國后,原定6月的拜登首次中東行又被推遲到7月中旬,內心焦急的美國只好先放風說,“沙特在過去的80年中始終是美國的戰略伙伴,歷任美國總統也都曾與沙特領導人進行會晤”。既要給美國盟友的“面子”,又要維持與俄羅斯合作的“里子”,以沙特為首的海灣合作委員會(海合會)國家的做法愈發耐人尋味。中東戰爭期間,沙特等產油國成為影響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一個變量,半個世紀之后,這些中東產油國又成為“新的變量”,以更加不卑不亢的姿態捍衛自身利益,甚至有的已從學術層面開始謀劃“后俄烏沖突時代”的糧食、軍事、科技等方面的自給自足。
沙美有“嫌隙”,但談不上“交惡”
一段時間以來,有關沙美關系存在不確定性乃至“交惡”的論斷不絕于耳,特別是針對“卡舒吉遇害案”,拜登對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王儲的批評和有意疏遠致使兩國關系陷入低谷。報道王儲拒絕就石油增產與拜登通話時,沙特輿論也有類似的評論。但據筆者觀察,以及與沙特一些政治分析人士交流的情況看,所謂“交惡”只是一種對表面問題的過度解讀。有沙特分析人士表示,沙特政府對奉行“價值觀外交理念”的美國民主黨政府歷來沒什么好感,近來雙方關系表面上的“嫌隙”在本質上也是這種現象的延伸。在沙特人看來,造成這種“嫌隙”不斷發展的更深層原因,是沙特越發認識到美國的中東政策厚此薄彼,且并不具備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近日,沙特海灣研究中心主席阿卜杜勒·阿齊茲·薩格爾在沙特“新聞”電視臺一檔訪談節目中對美國政府表達了不滿。他首先羅列了奧巴馬、特朗普和拜登三屆政府對伊朗核問題采取的立場,然后總結了美國的“四宗罪”:第一,“改變既定政策、違背以往承諾的是美國,使我們無法判定其未來走向,而沙特奉行的是穩定、持久的政策”,“沙特與其他海灣阿拉伯國家一道,迫切需要了解美國政府針對以往承諾,特別是在事關地區安全的重要領域所做承諾的真實立場”;第二,美國國會在對外軍售的討論上往往給以色列特殊待遇,卻給沙特等國制造障礙,更試圖阻撓其實現軍事裝備自主、自足的戰略意圖;第三,美國當下對海合會國家的政策仍處于“戰術”而非“戰略”層面,體現在美方急于要求沙特增產石油、在俄烏爭端中強烈譴責俄羅斯,以及弱化同中國的聯系;第四,美方往往“口惠而實不至”,特朗普在上任伊始的訪沙行程中曾作出承諾,若沙特境內的石油設施遭襲,則美方勢必采取反擊措施,然而此后一段時間沙特遭到也門胡塞武裝襲擊,美方卻無動靜。
盡管拜登訪問沙特的行程被推延,但沙美兩國近日還是委派高級別代表前往會見對方領導人,雙方修復關系的意圖十分明顯。沙美之間既定和正在進行中的合作也在繼續。以應對伊朗和構筑海灣地區一體化防空體系為例,美國與以沙特為首的海合會國家仍保持高頻率的互動和交流。
筆者于2018年-2019年在沙特考察期間還發現,美方“深耕”沙特數十年,影響力不容小覷。“在沙特等海灣國家,主流認識中美國就是世界第一大國,未來一段時間也是如此。”交流中,有沙特青年這樣談論美國,他們直言,“美國通常還是我們出國留學的首選地”。記得筆者應邀參加沙特學者舉辦的家庭沙龍,席間有美國“科研”人員以流利的沙特方言闡述美國政府的對沙政策,在座的數十位沙特學者似乎已習以為常,但筆者的最大感觸是美方在對沙特的研究和籠絡上用了不少心。
盡管“耕耘”多年,但美國與海灣地區盟友體系的逐步弱化已是大勢所趨。據筆者觀察,從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沙特民間的對美情緒經歷了由一度“親近”和“關注”向“疏遠”和“無所謂”的明顯轉變,也不乏有民眾因不滿美國對沙政策而在社交媒體上稱“拜登是騙子”。對拜登政府而言,在民調持續低迷、中俄相繼強化與海合會國家關系的前提下,或許也清楚彌合與沙特的“嫌隙”、修復與海灣阿拉伯國家的整體關系是“費力且不討好”的無奈之舉。
“歐佩克+,把政治排除在決策之外”
面對不斷飆升的油價,拜登3月初向沙特和阿聯酋這兩個中東主要產油國尋求幫助,但兩國領導人都拒接美國總統的電話。美國媒體以此判斷,美國和中東產油國漸行漸遠。部分原因是拜登政府拒絕將也門胡塞武裝列入“恐怖組織”名單讓沙特、阿聯酋不滿,一些海灣國家還認為美國試圖重啟伊朗核協議的做法有損自身利益。
更重要的是,沙特和俄羅斯多年來一直主導著“歐佩克+”聯盟,共同控制能源生產以實現市場價格的穩定。3月29日,沙特能源大臣明確表示,歐佩克+將把政治排除在其決策之外,以支持穩定能源價格的“共同利益”。沙特對拜登當局的“不理睬”策略客觀上為俄羅斯在俄烏戰場與西方博弈增添了能源籌碼,普京政府也敏銳察覺到沙美“嫌隙”對俄而言是難能可貴的機遇,需要盡快加強與沙特政府的務實聯系。
回顧歷史,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后,為打擊對手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國家,沙特等中東產油國宣布石油禁運,暫停出口,讓當時原油價格從每桶不到3美元漲到13美元。第一次石油危機,讓西方國家經濟進入衰退期。沙特等國動用“石油武器”的做法,在當時也一度成為左右中東戰爭的變量之一。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說:“有史以來,還沒有一個由弱小國家組成的集團能迫使占人類絕大多數的其他國家的人民如此戲劇性地改變生活方式,而遭到的抗議卻如此之少。”
“世界必須擺脫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沙特和阿聯酋是關鍵國際伙伴。”英國首相約翰遜3月在閃電訪問沙阿兩大產油國,試圖游說它們增產時這樣表示。但這些中東產油國沒有完全按照美英等國的想法,在俄烏危機中動用“石油武器”。科威特學者穆罕默德·拉米希日前在沙特重要學術刊物《觀點》撰文稱,海灣阿拉伯國家自俄烏沖突爆發以來采取了“并不完全一致但大體中立”的立場與做法:時任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的阿聯酋首先以反對票的形式拒絕譴責俄羅斯,后又與其他海合會國家一起在聯合國大會上支持了譴責;阿聯酋、埃及、伊拉克等國外長還到訪莫斯科,試圖了解其真實意圖,為烏克蘭危機尋找政治解決方案;科威特對俄羅斯的“占領行為”表達了譴責,而沙特則僅僅通過薩勒曼國王援助中心向受戰爭影響的烏克蘭難民提供了援助。但總體而言,作為美國傳統盟友的海合會國家僅以不具備約束力的口頭譴責形式附和了西方對俄羅斯的不滿,卻沒有讓自身站在沖突任何一方的對立面。
更加值得玩味的是,隨著沙特與卡塔爾關系的修復,在海合會國家一體化進程再度迎來發展機遇的背景下,海灣阿拉伯國家敢于向美國及其西方盟友的訴求說“不”,并且充分認識到美方對俄制裁首先犧牲的是其歐洲盟友的利益,因此不可持續,這也在無形中提高了能夠左右石油價格的海合會國家的戰略影響力。
有關此番沙特、阿聯酋等國“硬氣”彰顯的深層原因,蘇丹籍沙特觀察家、《中東報》資深媒體人拉赫曼·優素福告訴筆者:“近來沙特開始不懼美國的施壓,是出于其自身實力的考量。作為G20成員的沙特朋友眾多,中國、俄羅斯以及許多國家都是其重要伙伴。實際上,早在奧巴馬執政時期沙特就不再過分在意來自美國的壓力,沙特試圖建立的是戰略層面的盟友關系,意味著盟友應彼此關切對方的利益。既然拜登計劃要訪問沙特和以色列,就應該明白沙特的擔憂、關切沙特的安全,不存在沒有付出的收獲。”
提早布局“后俄烏沖突時代”
拉赫曼·優素福還對筆者說:“當美國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向沙特施壓時,沙特會提醒美方,‘沙特尚有很多大國和盟友可以合作’,以此換取美方恢復理智。”在筆者看來,在現實利益的驅動下,沙特政府會在沙美同盟框架下繼續奉行多元化的外交政策,同包括中俄等國強化關系,以使自身掌握博弈的話語權。
自俄烏沖突爆發以來,沙特、阿聯酋等海灣產油國正逐漸被國際輿論視為“能夠影響國際格局的新變量”,并給其他國家帶來不少啟示。最新一期沙特《觀點》的卷首語中這樣寫道:“俄烏戰爭并不是簡單、尋常的事件,它更像一場撼動世界的大地震,其在各領域帶來的影響幾乎波及世界所有國家,因此足以影響乃至改變國際社會的舊格局,盡管建立中的新格局至今仍不明朗。”該刊還提到,隨著俄烏沖突進程的延伸,一種早在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之后便逐步消逝的“極化”現象愈發清晰、正在逐步嶄露頭角,而海灣阿拉伯國家之所以能夠以“最大限度的溫和、智慧和中立”應對俄烏局勢的發展,秉持和平、對話解決爭端的原則,首先源于其與沖突各方(直接或間接)均建立了戰略關系,其次由于其本身能夠左右國際能源市場,第三則因為其以中立和現實主義為基礎制定并奉行國家政策。
在中東媒體上,很多阿拉伯學者撰文說,“后俄烏沖突時代”的海灣國家應及時布局,著力實現糧食和軍事裝備的自給自足。
在筆者看來,這種尋求擺脫傳統制約、實現安全自主、糧食和科技自給自足的海灣地區總體氛圍,從根本上有利于有關國家“以小博大”,而這種對擺脫能源、糧食依賴,轉向多元發展的清晰認識,對國際政治和經濟格局而言原本就是值得關注的“新變量”。近年來,沙特等海灣國家力圖強化同中國在汽車工業、人工智能等科技產業領域的合作,也引起了西方國家的關注。
圍繞與美俄中三個影響國際格局最重要國家的交往和關系,沙特科研與知識交流中心首席學者、俄中問題專家阿卜杜拉·法拉吉告訴筆者:“決定沙特與中美俄‘三角’支柱關系的,是每一‘角’所具備的實力。從建國初始,沙特就能夠根據變換中的實力格局適時調整方向。當下,中俄被看成正在挑戰美國的地位,而美方也在應對這一挑戰,沙特則將以前人的經驗為基礎,及時調整自身與各國的關系,以適應變化中的國際格局。”
不難看出,沙特及其影響下的海灣阿拉伯國家將繼續奉行多元化的外交政策,但這些中東產油國并不是在任意場合都愿意無條件附和“多邊主義”倡議。縱觀現代沙特建國近百年的發展史,結合海合會國家一體化建設的總體進程,一種濃郁的從“慕強”“從強”到“自立自強”的心態存在于海灣地區阿拉伯民族的性格、國格之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左右著他們的行事風格和對外交往準則。
對中國來說,如何認知并與這一“新變量”拉近距離,在既有戰略關系的框架下不斷加強中國與沙特、中國與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之間的共建共享,都是重要的課題。
(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中阿改革發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沙特科研與知識交流中心訪問學者)
沙美有“嫌隙”,但談不上“交惡”
一段時間以來,有關沙美關系存在不確定性乃至“交惡”的論斷不絕于耳,特別是針對“卡舒吉遇害案”,拜登對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王儲的批評和有意疏遠致使兩國關系陷入低谷。報道王儲拒絕就石油增產與拜登通話時,沙特輿論也有類似的評論。但據筆者觀察,以及與沙特一些政治分析人士交流的情況看,所謂“交惡”只是一種對表面問題的過度解讀。有沙特分析人士表示,沙特政府對奉行“價值觀外交理念”的美國民主黨政府歷來沒什么好感,近來雙方關系表面上的“嫌隙”在本質上也是這種現象的延伸。在沙特人看來,造成這種“嫌隙”不斷發展的更深層原因,是沙特越發認識到美國的中東政策厚此薄彼,且并不具備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近日,沙特海灣研究中心主席阿卜杜勒·阿齊茲·薩格爾在沙特“新聞”電視臺一檔訪談節目中對美國政府表達了不滿。他首先羅列了奧巴馬、特朗普和拜登三屆政府對伊朗核問題采取的立場,然后總結了美國的“四宗罪”:第一,“改變既定政策、違背以往承諾的是美國,使我們無法判定其未來走向,而沙特奉行的是穩定、持久的政策”,“沙特與其他海灣阿拉伯國家一道,迫切需要了解美國政府針對以往承諾,特別是在事關地區安全的重要領域所做承諾的真實立場”;第二,美國國會在對外軍售的討論上往往給以色列特殊待遇,卻給沙特等國制造障礙,更試圖阻撓其實現軍事裝備自主、自足的戰略意圖;第三,美國當下對海合會國家的政策仍處于“戰術”而非“戰略”層面,體現在美方急于要求沙特增產石油、在俄烏爭端中強烈譴責俄羅斯,以及弱化同中國的聯系;第四,美方往往“口惠而實不至”,特朗普在上任伊始的訪沙行程中曾作出承諾,若沙特境內的石油設施遭襲,則美方勢必采取反擊措施,然而此后一段時間沙特遭到也門胡塞武裝襲擊,美方卻無動靜。
盡管拜登訪問沙特的行程被推延,但沙美兩國近日還是委派高級別代表前往會見對方領導人,雙方修復關系的意圖十分明顯。沙美之間既定和正在進行中的合作也在繼續。以應對伊朗和構筑海灣地區一體化防空體系為例,美國與以沙特為首的海合會國家仍保持高頻率的互動和交流。
筆者于2018年-2019年在沙特考察期間還發現,美方“深耕”沙特數十年,影響力不容小覷。“在沙特等海灣國家,主流認識中美國就是世界第一大國,未來一段時間也是如此。”交流中,有沙特青年這樣談論美國,他們直言,“美國通常還是我們出國留學的首選地”。記得筆者應邀參加沙特學者舉辦的家庭沙龍,席間有美國“科研”人員以流利的沙特方言闡述美國政府的對沙政策,在座的數十位沙特學者似乎已習以為常,但筆者的最大感觸是美方在對沙特的研究和籠絡上用了不少心。
盡管“耕耘”多年,但美國與海灣地區盟友體系的逐步弱化已是大勢所趨。據筆者觀察,從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沙特民間的對美情緒經歷了由一度“親近”和“關注”向“疏遠”和“無所謂”的明顯轉變,也不乏有民眾因不滿美國對沙政策而在社交媒體上稱“拜登是騙子”。對拜登政府而言,在民調持續低迷、中俄相繼強化與海合會國家關系的前提下,或許也清楚彌合與沙特的“嫌隙”、修復與海灣阿拉伯國家的整體關系是“費力且不討好”的無奈之舉。
“歐佩克+,把政治排除在決策之外”
面對不斷飆升的油價,拜登3月初向沙特和阿聯酋這兩個中東主要產油國尋求幫助,但兩國領導人都拒接美國總統的電話。美國媒體以此判斷,美國和中東產油國漸行漸遠。部分原因是拜登政府拒絕將也門胡塞武裝列入“恐怖組織”名單讓沙特、阿聯酋不滿,一些海灣國家還認為美國試圖重啟伊朗核協議的做法有損自身利益。
更重要的是,沙特和俄羅斯多年來一直主導著“歐佩克+”聯盟,共同控制能源生產以實現市場價格的穩定。3月29日,沙特能源大臣明確表示,歐佩克+將把政治排除在其決策之外,以支持穩定能源價格的“共同利益”。沙特對拜登當局的“不理睬”策略客觀上為俄羅斯在俄烏戰場與西方博弈增添了能源籌碼,普京政府也敏銳察覺到沙美“嫌隙”對俄而言是難能可貴的機遇,需要盡快加強與沙特政府的務實聯系。
回顧歷史,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后,為打擊對手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國家,沙特等中東產油國宣布石油禁運,暫停出口,讓當時原油價格從每桶不到3美元漲到13美元。第一次石油危機,讓西方國家經濟進入衰退期。沙特等國動用“石油武器”的做法,在當時也一度成為左右中東戰爭的變量之一。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說:“有史以來,還沒有一個由弱小國家組成的集團能迫使占人類絕大多數的其他國家的人民如此戲劇性地改變生活方式,而遭到的抗議卻如此之少。”
“世界必須擺脫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沙特和阿聯酋是關鍵國際伙伴。”英國首相約翰遜3月在閃電訪問沙阿兩大產油國,試圖游說它們增產時這樣表示。但這些中東產油國沒有完全按照美英等國的想法,在俄烏危機中動用“石油武器”。科威特學者穆罕默德·拉米希日前在沙特重要學術刊物《觀點》撰文稱,海灣阿拉伯國家自俄烏沖突爆發以來采取了“并不完全一致但大體中立”的立場與做法:時任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的阿聯酋首先以反對票的形式拒絕譴責俄羅斯,后又與其他海合會國家一起在聯合國大會上支持了譴責;阿聯酋、埃及、伊拉克等國外長還到訪莫斯科,試圖了解其真實意圖,為烏克蘭危機尋找政治解決方案;科威特對俄羅斯的“占領行為”表達了譴責,而沙特則僅僅通過薩勒曼國王援助中心向受戰爭影響的烏克蘭難民提供了援助。但總體而言,作為美國傳統盟友的海合會國家僅以不具備約束力的口頭譴責形式附和了西方對俄羅斯的不滿,卻沒有讓自身站在沖突任何一方的對立面。
更加值得玩味的是,隨著沙特與卡塔爾關系的修復,在海合會國家一體化進程再度迎來發展機遇的背景下,海灣阿拉伯國家敢于向美國及其西方盟友的訴求說“不”,并且充分認識到美方對俄制裁首先犧牲的是其歐洲盟友的利益,因此不可持續,這也在無形中提高了能夠左右石油價格的海合會國家的戰略影響力。
有關此番沙特、阿聯酋等國“硬氣”彰顯的深層原因,蘇丹籍沙特觀察家、《中東報》資深媒體人拉赫曼·優素福告訴筆者:“近來沙特開始不懼美國的施壓,是出于其自身實力的考量。作為G20成員的沙特朋友眾多,中國、俄羅斯以及許多國家都是其重要伙伴。實際上,早在奧巴馬執政時期沙特就不再過分在意來自美國的壓力,沙特試圖建立的是戰略層面的盟友關系,意味著盟友應彼此關切對方的利益。既然拜登計劃要訪問沙特和以色列,就應該明白沙特的擔憂、關切沙特的安全,不存在沒有付出的收獲。”
提早布局“后俄烏沖突時代”
拉赫曼·優素福還對筆者說:“當美國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向沙特施壓時,沙特會提醒美方,‘沙特尚有很多大國和盟友可以合作’,以此換取美方恢復理智。”在筆者看來,在現實利益的驅動下,沙特政府會在沙美同盟框架下繼續奉行多元化的外交政策,同包括中俄等國強化關系,以使自身掌握博弈的話語權。
自俄烏沖突爆發以來,沙特、阿聯酋等海灣產油國正逐漸被國際輿論視為“能夠影響國際格局的新變量”,并給其他國家帶來不少啟示。最新一期沙特《觀點》的卷首語中這樣寫道:“俄烏戰爭并不是簡單、尋常的事件,它更像一場撼動世界的大地震,其在各領域帶來的影響幾乎波及世界所有國家,因此足以影響乃至改變國際社會的舊格局,盡管建立中的新格局至今仍不明朗。”該刊還提到,隨著俄烏沖突進程的延伸,一種早在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之后便逐步消逝的“極化”現象愈發清晰、正在逐步嶄露頭角,而海灣阿拉伯國家之所以能夠以“最大限度的溫和、智慧和中立”應對俄烏局勢的發展,秉持和平、對話解決爭端的原則,首先源于其與沖突各方(直接或間接)均建立了戰略關系,其次由于其本身能夠左右國際能源市場,第三則因為其以中立和現實主義為基礎制定并奉行國家政策。
在中東媒體上,很多阿拉伯學者撰文說,“后俄烏沖突時代”的海灣國家應及時布局,著力實現糧食和軍事裝備的自給自足。
在筆者看來,這種尋求擺脫傳統制約、實現安全自主、糧食和科技自給自足的海灣地區總體氛圍,從根本上有利于有關國家“以小博大”,而這種對擺脫能源、糧食依賴,轉向多元發展的清晰認識,對國際政治和經濟格局而言原本就是值得關注的“新變量”。近年來,沙特等海灣國家力圖強化同中國在汽車工業、人工智能等科技產業領域的合作,也引起了西方國家的關注。
圍繞與美俄中三個影響國際格局最重要國家的交往和關系,沙特科研與知識交流中心首席學者、俄中問題專家阿卜杜拉·法拉吉告訴筆者:“決定沙特與中美俄‘三角’支柱關系的,是每一‘角’所具備的實力。從建國初始,沙特就能夠根據變換中的實力格局適時調整方向。當下,中俄被看成正在挑戰美國的地位,而美方也在應對這一挑戰,沙特則將以前人的經驗為基礎,及時調整自身與各國的關系,以適應變化中的國際格局。”
不難看出,沙特及其影響下的海灣阿拉伯國家將繼續奉行多元化的外交政策,但這些中東產油國并不是在任意場合都愿意無條件附和“多邊主義”倡議。縱觀現代沙特建國近百年的發展史,結合海合會國家一體化建設的總體進程,一種濃郁的從“慕強”“從強”到“自立自強”的心態存在于海灣地區阿拉伯民族的性格、國格之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左右著他們的行事風格和對外交往準則。
對中國來說,如何認知并與這一“新變量”拉近距離,在既有戰略關系的框架下不斷加強中國與沙特、中國與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之間的共建共享,都是重要的課題。
(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中阿改革發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沙特科研與知識交流中心訪問學者)